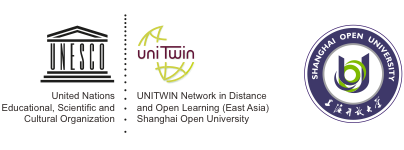(2003年11月6日,上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事务助理总干事 约翰·丹尼尔
——特以此纪念沃尔特·莱因·麦克唐纳·佩里(1921-2003)
导言
特别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演讲者常常这样说。但对我而言,这一事件实在非常特殊——我为能在此做主题报告而深感荣幸。
当我在十年前使用巨型大学(MegaUniversity)这一词汇时,我并不知道它会进入英语而且成为世界各地教育词汇表中的一个新的术语。我也没有想到十年后我会来参加巨型大学的首届高峰会议。我要极大地感谢中国和上海开放大学所做的这一创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很高兴支持这一会议。
我为我的发言选取了如下的标题,巨型大学: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巨大冲击。因为我负责引进了巨型大学这一新的词汇。你们可以理解,今天早上我的论述将融合我个人的反思和专业分析。
相当巧合的是,我以终身学习的精神选学的一门课程,成了我首次接触一所大型的远程教学大学和我发明巨型大学这一术语之间的联结点。在1971年,我的第一个学术职务是冶金工程的助理教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大学的埃库尔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工作。在我的漫长的教育经历——在牛津(Oxford)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和在巴黎(Paris)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终于开始从事作为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
我决定要好好地干我的教师职业,于是我想多了解一些教育对自己会很有帮助。在埃库尔工学院的工作使我很忙,所以我明白我必须业余学习。当时在蒙特利尔想这么做的最吸引人的机会,是圣乔治·威廉姆斯(Sir George Williams)大学开设的教育技术硕士课程计划。这是一个两年的全日制计划,包括一个实习期和一篇论文,但你也可以在晚上业余学习,我选择了后者。课程计划整体都很让人激奋,但使我改变人生的部分是实习。
实习期要求每个学生须在应用教育技术的教育机构中工作三个月。正当我开始考虑上哪儿去做我的实习时,一则重大革新的新闻突然传遍了整个国际教育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这是英国一所在1971年刚刚开始就招收了25,000名学生的新型大学,其特点是应用通信技术对住在各地的人们进行教学。该大学的章程中写道:“技术装备对高等教育是适当的”。
这听上去很激动人心,我致函询问我能否在开放大学实习。我将信函发给了大卫·霍格里奇(David Hawkridge)教授,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他答复说我将受到欢迎去那里做三个月的志愿工作者。让我在这里做个说明,正是这位大卫·霍格里奇,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支持下,后来与这里的中国人一起创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
埃库尔工学院非常友好地给了我三个月的假。于是我在1972年的夏天来到了弥尔敦·凯恩斯(Milton Keynes),在这个初创的大学工作。尽管当时只是办学的第二年,却已经拥有了4万名学生。那段短暂的实习期为我揭示了一场教育界令人震惊的革命。我整个地被学校的规模、理念、学生的投入、通信媒体的应用、以及整个系统的效率和效益所折服。我明白我在寻找高等教育的未来,我希望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
沃尔特·佩里:规模的竞争
我不去回忆我与开放大学副校长沃尔特·佩里的会面,在实习期间我感受到他对整个大学的影响。你们可能知道,沃尔特·佩里,后来被尊称为圣沃尔特·佩里,随后是沃尔特·佩里阁下,在今年年初去世了。我将我的这一次发言用以纪念他,是因为他对奠定今日巨型大学的基础比任何人的贡献都大。我们得以启用“巨型”这个词来称呼这些院校,应该说极大地得益于他。
开放大学的创办是有争论的。该计划本是哈罗德·威尔逊大脑的产儿,他在1964年成为英国首相。尽管他对他起初命名的“播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Air)”作了极大的承诺,但该项目从未成为他所属的政党,即工党的官方政策。威尔逊组建开放大学的程序多少有点超出正规的政府部门结构,而将一些特别卓越的人士组合成一个规划委员会。他们决定新的大学不应该被命名为“播送大学”,因为那样太注重大学使用的方法,而是取名开放大学。这个校名强调了这一创举的根本目的,即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机会。
部分是因为上述规划过程发生在正规的政府体制之外,部分还因为委员会成员是一些谨慎的保守的人士,教育部的公务员们对威尔逊的激进的革新表现出深深的怀疑。他们表示了他们的怀疑主义,并要求当时被任命为开放大学副校长和行政首脑的沃尔特·佩里先组织实施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看看远程教学系统是否可行。
对于今天聚集在“巨型大学上海峰会”的我们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沃尔特·佩里没有考虑这一建议。我相信他这样做持有双重理由。即使在早期,他就已经懂得远程学习的巨大价值在于其规模运行的潜力。他已经看到创建一所开放大学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但是他同样也看到如果能够实现规模运行,那么每个新增学生的边际成本有可能比传统院校的要低。因此他懂得,如果他启动一个只有几百学生的小规模试点项目,每个学生的成本将是巨大的,而人们可能因此嘲笑整个理念。
于是,他开始的第一年招生就是25,000,超过了当时英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在校生总数。事实上,仅仅在几年前,当哈罗德·威尔逊声称要创办播送大学时,全英国大学学生总共也只有13万。
他一开始就做大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性的。他敏感地认识到从在职成人那里有巨大的被抑制的大学学习的需求,相当数量的成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懂得,如果有一个相当可观数量的这类人员开始在开放大学学习,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强大的、政治上活跃的追随者。而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实。
当我在开放大学运行的第二年来到该校实习时,当时已经有4万学生了。他们几乎全都是开放大学的狂热支持者,因为开放大学给了他们实现高等教育的第二次机会。开放大学学生和员工的热情是极富感染力的,当我在1972年结束我在开放大学的三个月的实习期时,我已经热切地期望能够加入这一远程学习的新的运动。
随着魁北克远程大学(Quebec’s Tele-University)的创建,机会几乎马上降临。我在那儿度过了四年愉快的时光(1973~1977),随后前往阿尔伯塔(Alberta)省的阿萨巴斯卡(Athabasca)大学。从那里开始我被大学领导的职能所吸引,在安大略(Ontario)省的劳伦梯安(Laurentian)大学担任了一个时期的校长后,我使自己在1990年回到了开放大学并成为该校的副校长。我是沃尔特·佩里这一职位的第二任后继者。不到20年,我从一位领取最低薪水的开放大学雇员——因为是实习期,事实上我并不领取薪金,晋升成为领取最高薪金的成员。
终身学习的收益
也许是因为我在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对教育技术的学习为我的人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我继续作为一名终身学习者,在过去的20年中以学生的身份从四所大学选学了远程学习课程。然而,我现在必须做出一个令人难堪的坦白。70年代早期,我在圣乔治·威廉姆斯大学学习教育技术,之后因工作从蒙特利尔移居魁北克城,随后是阿尔伯塔省西部,使我没有完成论文和取得学位就放弃了硕士课程计划。
90年代早期,也就是我在开放大学开始就职的那个时期,我从加拿大的一所大学学习神学并取得文凭之后,想学习某种新事物的欲望再次闪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想学习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法律学位。然而,当我将我的想法告诉我妻子时,她和我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结束时,我妻子向我说明我从领导开放大学职位上剩下来的时间极其有限,她恼火地对我说:“好了,如果你实在想再当一次学生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完成教育技术学位的学习?那是你远在70年代就没有完成的一件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富有灵感的想法,于是就写信给圣乔治·威廉姆斯大学,现在已经成为科考迪亚(Concordia)大学,申请再次注册学习。他们回复了一份十分友好的信函。信中说,他们通常并不允许人们在中断了这么长时间后继续课程计划,并且说我在20年前学习的大多数课程现今被认为已经过时。然而他们的结论是,由于我已经在我后来的人生中应用了我在70年代课程计划中学习到的东西,作为特例,可以允许我再次注册以便撰写论文。
在1972年,蒙特利尔的一所大学给我带薪的假期前往开放大学实习。在1995年,开放大学赐予我一个月的带薪假期让我得以回到蒙特利尔当一名学生。这里有一种美妙的对称。我要愉快地说,我完成了我的论文和我的学位。在1996年春天的毕业庆典上,我特别高兴自己是一位新的毕业生,和其他毕业生一起坐在大厅的后排。那是因为在那一年的同一个季节,我在大多数的星期六都在主持开放大学的学位授予庆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学位授予庆典是很美好的。
完成教育技术硕士学位,我前后整整经历了25年时间,所以这也是在工作中进行终身学习的一个案例。这一案例对我而言,还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验,因为它让我回到反思和研究中去,这对我这个成天忙于分析和行动的开放大学副校长来说,实在是一种美妙的变换。我高兴地将论文扩展成了专著,并且愉快地看到了出版的成功。
对巨型大学的认同
我决定将我的论文专注于论述远程教学大学在应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方面面临的挑战。当时,这正是我这个作为开放大学的行政首脑面对的最大的战略挑战。然而,当我开始探讨这一问题时已经明白,大型远程教学大学面临的挑战在许多方面与小型远程教学院校面临的挑战不一样,而且与那些只是想将新技术的应用整合到校园教学中去的大学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
我需要用一个词汇来描述我试图研究的一组有限的大学,巨型大学一词成了恰当的选择。我使用这一术语来专指那些以远程教学为主要使命的大学,而且其同时注册的学位层次计划的学生数必须超过10万。10万这一数字是一个随意的限额值,然而它在1995年是一个适合当时实际的一种准则。我不记得当时有哪一所远程教学大学拥有的学生数介于6万与10万之间。
我的准则使我确认了11所院校: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the China TV University System);法国的国家远程教育中心(the Centre National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西班牙的国立远程教育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Educación a Distancia);南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韩国国立开放大学(the 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印度尼西亚的特布卡大学(Universitas Terbuka);英国开放大学(the UK Open University);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伊朗的帕亚莫·努尔大学(Payame Noor University);泰国的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Sukhothai Thammathirat Open University)和土耳其的阿那都鲁大学(Anadolu University)。
我并不试图描绘一张当今巨型大学的列表,但我希望,也许作为这次高峰会的一个成果,有人会继续跟踪这一发展。同我在90年代撰写我的专著时不同,现在有相当一个数量的院校拥有学生数在5万至10万之间。自从我撰写那本书以来,也已经有一些院校的学生数超过了10万这一标志数额,比如巴基斯坦的阿拉玛·伊克拜尔开放大学(the Allama Iqbal Open University)和印度一些邦的开放大学。我也关注私立的、盈利性的虚拟大学的出现,如美国的凤凰在线(Phoenix Online)。依据其当前的增长率,这一院校的学生数应该很接近10万这一标志数额了。
巨型大学的冲击
巨型大学正在增长和多样化,但它们有什么成就?其成就能否帮助我们探讨和解决当今时代重大的教育问题?我确信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我认为过去50年间没有哪一项教育革新在其对问题解决的影响力方面可以同大规模的远程学习大学——即巨型大学相比。
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呢?我发现用我称之为教育永恒的三角形来表述这些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三角形由三个矢量组成:机会矢量,成本矢量和质量矢量。我只需稍作说明来论证我选择这些挑战的合理性。教育机会依然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面临的首要问题。问题就在于教育是一项人权,也是人类发展、社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根本道路。如果人们无法接受教育,那他们自己及其所在的社区就会陷于更贫困的生活。
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我们的成员国,为那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或者没有接受到足够教育以便使他们走上满意生活道路的千百万儿童提供就学机会。问题已经映射到高等教育,世界人口的一个很大的比例在20岁以下,如今已经满足不了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将很快遭到更大的需求狂潮的冲击。
机会的缺少同我的第二个矢量成本有关。机会不够的部分原因是成本太高。发展中国家大学的案例是非常清楚的。殖民政权的一个遗产是大学的模式实在太昂贵,以至难以扩大来满足一个需要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很高的时代的需求。
最后,我的三角形的第三个矢量是质量。它是与上述两个矢量紧密相关的。直到出现巨型大学之前的整个历史表明,在质量和排他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公众都深信,只有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才能实现高质量。这部分地源自这样一种信念:高质量教育必定是成本高的教育。
我们的巨型大学是否重塑了这个三角形?它们是否打破了质量和排他性之间的可悲的联系?它们是否能够在降低成本、保持或改善质量的同时增加机会?如果真是这样,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对该问题的答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极为重要:这些方法是否适用于其它层次的教育?
我相信,成功的证据是清楚的。你们只需要看一看巨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可以看出它们对扩大教育机会的巨大贡献。我在早些时候指出过:今天英国开放大学一个学校的学生数就比仅仅40年前英国所有大学合在一起的学生总数还多。如果你们将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各邦的开放大学的学生数加在一起,我相信比若干年前所有印度大学的学生总数还多。
但是我们的批评者会说:增加机会是容易的。问题在于成本如何,特别是质量如何?我得承认我未能掌握有关巨型大学成本的最新文献,这类文献在过去的10年中增长得很快,特别是在印度。经济学家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将问题复杂化,开放大学的成本分析也不例外。计算大学的投资和运行成本相当直截了当,但如果你们尝试考虑整个社会的所有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变得非常困难。
举例说,许多巨型大学的学生是在职的,他们通过工作和纳税继续对国民经济作出贡献。这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在另一方面,因为巨型大学的学生通常年龄较大,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对社会贡献出他们学习的所得的时间比之年轻的毕业生要短一些。所有这类考虑都是重要的,巨型大学应该保持对成本作最新的研究。然而,我满意的是,你们几乎所有的计算都表明,巨型大学每个学生的总成本远远低于传统大学。
例如,在90年代,英国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对成本进行独立核算,结果发现开放大学一个学位的成本大约是传统院校的60~80%。我相信在其它巨型大学这个差别可能更大。事实上,在我撰写我的《巨型大学》一书时,我发现对印度尼西亚的特布卡大学而言,尽管其毕业率很低,但每个毕业生的总成本却是传统大学成本的三分之一,而每个毕业生的国家成本则不足其它地方成本的30%。
另一个证据在于某些巨型大学——我想比如泰国的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在大学本科生教育层次上国家基本上是不投资的。事实上,我还应该一提的是香港公开大学的案例。香港公开大学离巨型大学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它已经基本上不要求香港政府对其运行成本进行财政支持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质量。巨型大学是否为它们的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而且这些学生是否以较大的比例通过了他们的课程和学位学习?首先,我们要明白,对巨型大学而言,质量并非一个自动拥有的特征。不存在一种模式,不需要努力就能赢得质量。问题在于,巨型大学能否在不牺牲增加机会和降低成本的同时赢得高质量?
我提起过特布卡大学的案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诚实的: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局建立该校时,他们并没有期待它将是一所高质量的学校。我相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韩国国立开放大学。在其早期,政府只是试图通过提供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为成千上万名从扩展的学校系统中产生的年轻人提供一种安全阀门。现有的大学无法满足这一需求,需要一种大规模的解决方案,用来吸收无法进入其它大学的年轻人。你们可以说,它们建立起来实现低质量运行。然而,在其它地区,质量是首先要考虑的。比如在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努力成为质量的灯塔,并且向传统大学的粗制滥造的函授学校证明:远程学习可以做得很好。事实上,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承担了一种管理其它院校的角色,为了能够帮助它们完善它们的质量。
在英国的情形也是这样,那些建立了开放大学的人们决定,开放大学必须做得同最好的一样好。但是,愿望并不等于实绩。我希望这次高峰会的讨论议题之一是:相对于你们国家的质量保证体系,你们院校的实绩如何?我能够直说的是:英国开放大学创建者们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我高兴的是在我2001年离开英国开放大学时,依据一个国家批准的独立机构所做的教学项目评估,开放大学名列全英国100多所大学中的第10位。
我更高兴的是,自从我离开后,英国开放大学的排位在继续提升,如今已经名列第6位了。如果你们记得某些人在30年前嘲笑英国开放大学和其它巨型大学的创办,上述结果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你们将对质量和机会的矢量结合起来,这个冲击则更惊人。同其它巨型大学一样,英国开放大学拥有大量的学生。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们将在评估中赢得优秀的不同学科的计划项目学习的英国大学学生数累计相加,你们就会发现诸如音乐、地球科学和社会政策等这些学科,在优秀计划项目学习的所有学生中的大多数是开放大学的学生。
但是,我回到我早些时候的观点。质量和优秀从来不会自动生成。然而,我确实察觉到,那些一开始在质量上没有很大雄心的巨型大学,已经感受到别的巨型大学范例的启示。如今看来,所有国家都在鼓励它们的巨型大学追求高质量,因为它们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巨型大学能够而且已经实现了一场教育革命,即同时实现增加机会、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我的永恒的三角形已经以一种对人类充满巨大希望的方式被重新建构。
巨型大学的秘密
我的结束语将谈及我相信的巨型大学是如何做到上述一切的。它们的秘密是什么?
同某些批评者所说的相反,它们并非通过将教育非人性化来实现这一切的。巨型大学并非没有灵魂的教育工厂。它们所做的是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人的、技术的和组织的要素组合了起来。它们理解并赢得了人类学习的基本特征这一优势。
学习是两类活动的综合。首先,需要学习者独立自主的活动,例如阅读书籍、看电视节目、听讲课或录音带、写论文、计算机上工作或进行数学计算。这些活动构成了学生学习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在高等教育是如此。它们也正是那些允许我们利用技术来增加机会、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活动,而这是关键。这是由于独立学习的基本工具,例如印刷品、计算机课件、音频材料和电视节目,一旦你们已经投资开发出第一份原型,大量复制的成本相对很低;大容量帮助增加机会并降低成本;这也允许你们去提高质量,因为一旦你们实现了材料的规模生产,你们就有力量投资将它们做成精品。
然而证据表明,大多数学习者并不孤立地从事独立活动。技术必须包括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系统。你们还需要交互活动。“交互”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词汇而且被到处滥用。我应该用交互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境:某一学生的一项活动引起了另一个人的响应——可以是一位教师,一位辅导人员,或另外一位学生——对那个特定的学生就是具体的,确定的。今天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你们在听我讲话,你们每个人都被包括在独立学习中。当我结束演讲时,你们向我提出问题和评论,那就是一种交互活动。其它的交互活动包括有其他学生或辅导教师参加的面授环节,教师对你的作业进行批改和做出评论,通过电话提问题,对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调查做出响应,以及其它等。
这类活动对大多数学生的成功非常重要。但是,它们的成本较高,因为它们并不像独立学习那样以同种方式实现规模经济。制作20份光盘的复制盘成本很低,而追加的交互活动则要求更多的人员投入。
相信独立活动和交互活动之间的这一简单的区分在面对今日的挑战设计成功的教育系统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每一类活动拥有自己独特的成本结构。独立活动要求高的投资成本而边际成本很低;交互活动要求较低的投资成本但边际成本较高。你们可以整合两者,以便实现你们所希望的成本平衡。
两类活动对质量也做出不同的贡献。你们同时需要两者,所以主要的挑战在于努力将交互活动的成本结构尽量接近独立活动的成本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和互联网对于巨型大学是如此激动人心。大多数人称之为交互计算的技术并未真正实现交互,因为如果你和我敲击同一个键,我们将得到同样的响应。然而,我们现在可以展望计算机系统的未来,它们可以像一名优秀的辅导教师一样做出个别化的反应。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那将是另一场讲话的另一个故事。
我今天的目的是要直截了当地重申巨型大学代表了教育的革命,因为它实现了在整个历史上难以企及的教育目标,即教育更多的人、质量更好、成本更低。你们应该为你们巨型大学所达到的成就骄傲。巨型大学是对规模、成本和质量的一个巨大冲击。它们是所有人类的灵感之源,因为它在追求着一种实践教育的权利。